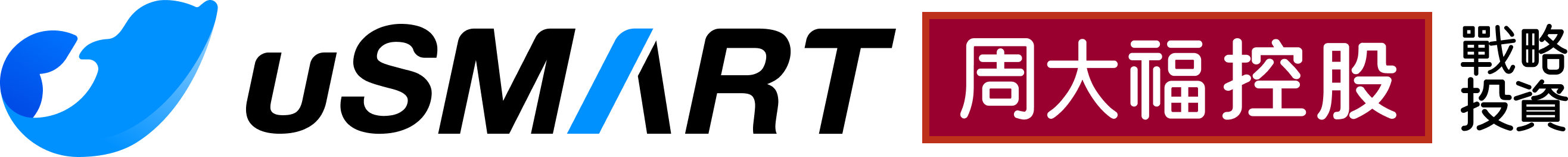美國時間1月11日美國參議院聽證會正式通過鮑威爾連任美聯儲主席、以及美聯儲理事佈雷納德升任爲副主席的提名。
近期海外市場對美聯儲提前加息甚至啓動縮表的擔憂,10年美債收益率從年初以來上行26bp(以實際利率上行爲主)並逼近1.80%,讓這次聽證會備受關注。
來源:覃漢投資筆記
鮑威爾釋放的鷹派信號雖未像12月會議紀要那麼超預期,但也進一步確認了美聯儲加快緊縮步伐的事實。聽證會中比較重要的表態如下:
①路線圖:3月底結束資產購買,年內加息,可能在年內晚些時候開始縮表;貨幣政策正常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②加息:如果高通脹持續時間比預期更長,美聯儲將會在更長時間內更多次加息,從而防止高通脹變得根深蒂固。
③縮表:尚未對縮表時點做出任何決定,傾向於用2~4次會議來討論縮表細節,並在未來幾次會議提供更清晰的指引;9萬億美元的資產負債表遠超所需水平,縮表將比上一次更早更快。
整體上,市場對這次聽證會的解讀相對溫和:開盤上行的美債利率和美元指數在聽證會開始後分別拐頭向下,10年美債利率下行2.7bp至1.739%,美元指數下跌0.37%,標普500和納指分別反彈0.92%、1.41%,COMEX黃金價格反彈1.26%。
但市場的加息預期幾乎沒有太多變動。對應到2022年3月、6月、9月、12月FOMC會議,市場定價隱含的累計加息次數分別爲0.85次、1.84次、2.64次、3.41次,即市場預期3月首次加息的概率爲85%、以及年內加息3~4次。

對於這次聽證會,我們的解讀如下:
第一,3月首次加息、7月縮表啓動的可能性在加大。目前1月提前結束資產購買的風險已經被鮑威爾排除。我們維持2021年加息3次的看法,此前我們的基準情形是6月、9月、12月分別加息1次並且2022年不會縮表,目前提前至3月、6月、9月,同時7月縮表啓動。
理由有五點:①高通脹風險: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誤判過通脹的美聯儲,爲了重塑政策公信力,更爲激進的緊縮姿態(至少在緊縮週期的初期)是必要的。此外,不同於疫情早期的影響機制,Omicron變異毒株似乎只會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短缺和供應鏈約束,導致高通脹難以消退。週三美國公佈的12月CPI同比很有可能突破7%。
②充分就業狀態基本實現。12月失業率超預期降至3.9%,低於美聯儲長期失業率目標4%,同時工資時薪增速超預期,意味着美聯儲重點關注的季度僱傭成本指數(ECI)將繼續創新高。
③金融條件仍過於寬鬆:即便短端利率對加息預期有所定價,但代表長期實際利率的10年TIPS利率仍深度爲負(-0.79%);本輪擴表週期,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佔GDP比重已達39%,遠超上一輪縮表前的水平23%。
④從工具儲備和應對經驗上說,美聯儲對這一次縮表的準備工作更充分,更早更快的縮表在操作上是可行的。
一方面,一級交易商可以通過向2021年7月美聯儲正式創設的常備回購便利(SRF)提供抵押品來獲得隔夜流動性(每日額度不超過5000億美元),從而避免重犯2019年縮表持續近兩年後出現「錢荒」的錯誤。
另一方面,目前美聯儲負債端的隔夜逆回購協議(O/N RRP)使用規模接近1.5萬億美元,銀行間流動性過剩的程度遠超2017年10月開始縮表前的水平,從而很大程度上推遲了縮表對銀行準備金餘額的衝擊。
⑤按照鮑威爾「傾向於用2~4次會議來討論細節」、12月會議紀要、以及部分美聯儲官員「在一兩次加息後便縮表」的表態,7月啓動縮表的概率較高。
回顧上一輪縮表,美聯儲在首次加息兩年後(加息4次)才啓動縮表(2017年10月),縮表方案的公佈(6月)比正式啓動提前了一個季度。縮表的方式是減少到期本金的再投資,而不是賣出,縮減的額度也是從最初每月100億美元在一年的時間內逐漸提高至每個月500億美元。
我們認爲縮表可能在6月會議宣佈,7月開始啓動,考慮到本輪資產負債表規模更大,縮減的最大額度可能爲每個月750億美元,縮表啓動後幾個月內逐漸提速至這一水平。
第二,10年美債利率上行壓力還未充分釋放,上半年破2%的可能性很大。我們此前在12月FOMC會議點評《更快的Taper,更早的加息》中提示,海外市場對未來美聯儲加息節奏加快已經有了一定預期,但對未來加息終點的預期可能仍不足。
爲何12月會議紀要公佈後,長端美債利率大幅上行?一是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內部對更早更快啓動縮表的共識,比鮑威爾在12月會議新聞發佈會上釋放的信號更強;二是根據紐約聯儲12月一級交易商和市場參與者調查,市場此前預計縮表最快在2023Q2啓動,10年美債利率2022Q1中位數預期爲1.75%,因此紀要提及縮表無疑導致市場被迫重新定價。
常識告訴我們,想要遏制高通脹和通脹預期,必須要讓名義政策利率上升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才能通過實際利率的上升給需求端降溫。12月FOMC會議美聯儲的經濟預測可能過於樂觀。一方面預測2022~2024年PCE同比增速將從2021年的5.3%回落至2.6%、2.3%、2.1%,但另一方面2024年底政策利率僅爲2.1%(累計加息8次),遠低於長期中性利率2.5%。
也就是說,美聯儲認爲即使加息加不到中性水平,通脹也能實現自然回落,而市場對本輪加息的終點水平預期比美聯儲更低,這就蘊含了潛在的超預期。一旦高通脹持續時間比預期更長,未來三年美聯儲的加息路徑將會更陡更高,市場雖正在重新定價,但可能還不夠,所以長端美債利率上行壓力還未充分釋放。

第三,美國貨幣緊縮預期進一步升溫,是不是意味着國內寬鬆空間受到限制?並非如此。
過去兩年多的行情告訴我們美債利率向國內利率傳導的機制並不順暢,一方面源於中美經濟、貨幣、金融週期的「三期錯位」,另一方面源於央行轉向「跨週期調節」。
目前驅動中美貨幣政策的底層邏輯依然迥異,高通脹風險迫使美聯儲不得不盡早開啓加息週期,而國內穩增長壓力使得央行需要「更加主動作爲」。中美利差只是貨幣政策差產生的「結果」而非「原因」,目前10年中美利差窄至103bp,但仍處於過去經驗中80~100bp的政策合意區間。
國內債市並非不瞭解貨幣政策「以我爲主」的基調,要不然也不會從12月下旬以來對降息預期進行「搶跑」交易,美聯儲緊縮信號對國內債市的擾動有限,更多是停留在「討論」層面,短期內寬貨幣仍是主線,而寬信用還只是遠期模糊的利空。